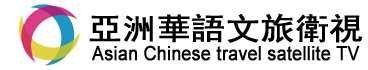近来常常思考一个中国画史上的问题“乱世人物”,其中,这个“乱世”在我这里也指的是“危世”,即风雨飘摇的鼎革之际。这里面有三个时代值得人们细思,一个是北宋“南渡”之后,一个是元末明初,一个是晚明清初。这三个历史时期,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其重大,北宋被迫南渡也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次南移,元末明初社会动荡很多知识分子选择了隐逸来避难,以保全自身,晚明清初的文化冲击是易代之后的文化坚守的问题,也是事关生死之大的名节问题。这三个历史节点所诞生的一批杰出的艺术家,都堪称后世宗师,比如“北宋”画院派画家李唐在南渡之后,画风大变,其代表作《采薇图》极象征士大夫的“不食周粟”的气节;又比如元代的倪云林在其晚年画作中所表现出的流离羁旅的苍凉之感;再比如由明入清之后的画坛巨子陈洪绶,那种生死煎熬之后,画作所表现出的对“古意”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的时代的不可逆转性,一方面在摧残着他们的文人士子心,一方面也极力促使着他们的艺术风范的形成。“乱世人物”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艺术感受,数百年之后,我们再回望他们的时候,也在审视着我们的时代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

晚明士夫的生死大节
晚明注定是一个充满激荡与恢弘,肆虐与背叛,无奈与挣扎的时代,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命运多舛则多与国家兴亡息息相关,如刘宗周、倪元璐、黄道周、钱谦益、王铎、朱耷等等,在大时代面前,他们每个人几乎都要直面一个问题:生与死!要么苟且偷生剃发易服做新朝的顺民,要么如刘宗周、黄道周那样以死全志不做贰臣,正如陈洪绶所言:“死非以外事,打点在胸中。生非意中事,摇落在桐风。” 当然,这里面除过王铎和钱谦益诸人,直面死亡时那种心里的怯懦以及对活着的苟且的希望,当年崇祯帝自缢之后,钱谦益在爱妻柳如是的协助之下做了南明的礼部尚书,清兵南下南京城破之日,歌伎出身的柳如是劝钱谦益和她一起投河自尽以不损名节,钱谦益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谦益硬托住了。于是钱谦益便腼颜迎降了,一起迎降的还有被后世倍加推崇的书法巨匠王铎。
世人解读陈洪绶或从其画风论其气象格调,或从其尚酒好色论其荒诞怪离,其实皆为媚俗媚时所需,谈论陈洪绶如果离开了他的士人之气,离开了他的家国之思,离开了他苟全于新朝心哀已死的心志就不可能触及陈洪绶的精神旨趣。虽然,清代毛奇龄有《陈老莲别传》载其:“顾生平好妇人,非妇人在坐不饮,夕寝非妇人不得寐;有携妇人乞画,辄应云。”也仅为其生平点缀而已,姑且以为不能以此而谈陈洪绶乃画坛好色之徒,今人多好此谈资,言陈洪绶则多言其风流韵事,在我看来这是对陈洪绶的不公。陈洪绶画作所彰显的那种高古超迈之境既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深究其画作背后的精神气象,则多让人体会到陈氏的用心良苦——“老莲(陈洪绶)刻意创造的高古境界,就是为了恢复绘画的正脉,那种被董其昌南北宗等弄乱的传统。”
熟知陈洪绶的学者知道,陈洪绶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9年)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官宦之家,祖父曾官至广东、陕西布政使,父亲则是一个屡试不第的秀才。他少年聪颖绝伦,从小喜欢丹青翰墨,朱彝尊的《陈洪绶传》载其:“年四岁”“画汉前将军关侯像,长十尺余。”“翁见侯相,惊下拜,遂以室奉侯。”四岁的时候,陈洪绶就表现出了惊人的人物造像能力,在萧山来斯行家见其墙面空白,便执笔画关羽,其造关羽像身材魁伟凤眼长须,栩栩逼真,来斯行一见大惊,以为关羽下凡常跪祭拜,为此还专门将房屋改为“关公祠”。陈洪绶早年习画令其师蓝瑛汗颜,毛奇龄《陈洪绶别传》载:“钱塘蓝瑛工写生,莲请瑛法传染,已而轻瑛。瑛亦自以不逮莲,终其身不写生,曰:‘此天授也!’” 蓝瑛说:“使斯人画成,(吴)道子、(赵)子昂均当北面,吾辈尚敢措一笔乎!”自愧在人物写生上力不及弟子陈洪绶。但这些被学者津津乐道的陈年往事,只能说明陈洪绶在艺术造诣上的天赋,但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大夫而言,家国之事才是顶天立地的大事,至于艺事何足挂齿耶!
陈洪绶早年在绍兴时,曾师事蕺山学派的开山之祖刘宗周。宗周之学黄梨洲在《明儒学案》中称其:“以慎独为宗,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宗周治学多注重体悟心证,恪守慎独二字。陈洪绶早年随其学多得教诲,其气质学养之根基皆从蕺山学派而来。刘宗周晚明时期士大夫恪守气节操守的代表,当年杭州失守之时,先生闻潞王降清,心情万分悲痛,欲效法伯夷叔齐绝粒而终,以全心志。先生说:“至于予之自处,惟有一死。先帝之变,宜死;南京失守,宜死;今监国纳降,又宜死。不死,尚俟何日?世岂有偷生御史大夫耶?”陈洪绶后来关于自我生死的拷问,多从先生而来,朱良志说:“国破之后,老莲(陈洪绶)碰到的是人生最基本也是最大的问题——‘生’的问题:他是不是还要继续活着?人的生命是唯一的,不可重复,但对于他来说,国破家亡,儒者的责任,理想的情怀,以及国破后老师(黄道周)、朋友(倪元璐、祝渊、祁彪佳)等都一一以死全志,深深地动摇了他的信念,使他基本失去了再活下去的理由。”
生死大节,既是儒者的大事,也是解开陈洪绶艺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源头。研究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如果脱离了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伦理思想,仅仅以艺术谈艺术,以技法谈技法,或者以今人之眼光揣度古人,皆是枉然。陈洪绶远远要比我们想象的痛苦的多,绝非一般论者所言风流倜傥的荒诞好色之徒,更非随意贴在他身上的“五百年来仅一人”的标签!

生死纠结下的艺术升华
的确对于晚明降清或者削发为僧的知识分子而言,常常纠结于生死之中,他们的精神世界是苍凉的,甚至是变态的,沦为新朝的工具之后,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快乐,遗民的指责以及自我良心的谴责,使得他们常常生不如死。是的,在事关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尊严的名节问题上,如洪承畴、钱谦益、王铎等极大地侮辱了读书人这个称谓,从小所受的孔孟之教在刀刃架在脖子上的那一刻,变得一无是处。陈洪绶与王铎不是一路人,王铎是真怕死,陈洪绶是在生死游离之间徘徊,王铎怕死才屈膝做了新朝的官,陈洪绶则是清兵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屈从,宁可削发为僧,宁可将自己在新朝变成一个“未死人”“废人”“弃人”,也绝不做新朝的犬!这是我敬佩陈洪绶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公元1644年,中国农历的甲申年,李自成兵破北京城,明王朝随着崇祯帝的自缢宣告结束,进而清兵大举入关,真正的灾难来临,次年战火蔓延至江浙一带,陈洪绶内心的平静完全被打破,加之恩师刘宗周、黄道周以及友人皆以身殉国,深深地动摇了他的信念,他说他的心底是“心事如惊湍”,内心的撕裂感与良知的拷问,让他不断地向自己发问:究竟是活着偷生还是以死全志?当他发此生死之问时,残酷的现实迅速地击碎了他高昂的理想,他身后有一大家子的生计问题等着他解决,还有尚未成年的儿女。无奈之下,他削发为僧以保留住自己作为明之遗民的体面,保留住中国知识分子最后的尊严!
但是,陈洪绶从未停止过对自己灵魂的拷问,他在诗中说:“国破家亡身不死,此身不死不胜哀!偷生始学无生法,畔教终非传教材。”“不死如何销岁月,聊生况复减青春。”“生死事不究,何必住于世。究之不忧勤,久住亦无济。”“龙华会上路茫然,误结浮生华酒缘。别去虽听座上语,夕阳西下听啼鹃。”这种生死煎熬,我深信对于一个饱受家国沧桑的知识分子而言是无比残忍,或许正是这样一边内心在挣扎,一边现实在鞭挞,构成了他入清之后游戏人间的性情,也促使了他对艺术表达的思考。因为,世间唯一可以聊寄此生的只有书画,他将所有的关于人生、关于家国、关于宇宙的思考全部浓缩成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作品当中。
陈洪绶的晚年完全接受了佛学思想,尤其是佛学当中的“不生不灭”的道理,因此,他试图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构建出一种超乎时间与空间的永恒,即朱良志先生所言的“他高古寂历的艺术,来表现宇宙和人生的‘不死感’”试图“将易变的人生放到不变的宇宙中展现它的矛盾,追问生命的价值,寻求关于真实的答案。”于是乎,陈洪绶入清之后的作品升华了,他的作品向着生命向着永恒在发问;于是乎,他创造一种高古的意境,高寒的艺术氛围,让古今画者难以企及。

高古的艺术背后关于永恒的信念
陈洪绶的朋友张岱曾在《陶庵梦忆》中评价好友陈老莲:“才足掞天,笔能泣鬼”而另一个好友周亮工则说:“章侯(陈洪绶)画得之于性,非积习所能致。昔人云‘前身应画师’,若章侯者,前身若大觉金仙,何画师之足云乎?”两位好友如此评价陈洪绶绝非溢美之词,从陈洪绶现存的传世作品来看确乎如此。
高古永恒之境在陈洪绶的作品当中,常常以画中的器物所展现,比如作于1649年的《蕉林酌酒图》所营造出来的时空永恒的氛围,芭蕉树下,一位书生老者背靠奇石若有所思,石案上放着锈迹斑斑的酒器,远处两位侍女正在烹菊煮茶,画面上的奇石、石案、酒器、祭器都可以看做是永恒不变,空间中唯一易变的就是人与芭蕉。陈洪绶酷爱芭蕉,是因为“芭蕉”是佛教中的法物,《维摩诘经》中说:“是身如芭蕉”,用芭蕉的易坏来隐喻人生的空幻无常,中国诗人也常常以“夜雨打芭蕉”来比喻人生的脆弱。陈洪绶有很多有芭蕉的作品,如《何天章行乐图》《品茶图卷》等等。
1651年的中秋节,陈洪绶与他的朋友饮酒西湖畔,大醉,便挥笔画下了《隐居十六观》的传世之作,并以此赠给他的好友沈颢。其中有一幅《醒石图》引人注目,一位隐士高枕石头,神情迷蒙似醉似醒,让人想起唐代李德裕甚好奇石,曾在他的平川别业中有“醒酒石”。陈洪绶画此图之真正用意,不在醒酒而在人生之醒悟,他有诗云:“几朝醉梦不曾醒,禁酒常寻山水盟。茶熟松风花雨下,石头高枕是何情?”人与石共老,不醒似醒!这是陈洪绶的高古之境。
在中国文化中,对“古意”一般有三重阐释,第一重如赵子昂所推崇的“尚古”之意,以先贤为师可为己镜;第二重是一种雅致复古之情,如清茶一杯,置于禅房,一本书一缕香的禅意生活;第三重是一种追求的境界,是指内在的精神旨趣,所企及的是生命的永恒,时间与空间的停留,这是陈洪绶的所抵达的精神彼岸。
其实,乱世中像陈洪绶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三个时期很多,他们既是时代的思考者,也是时代的受害者,他们不损名节坚守中正,宁可玉碎不能瓦全的气节是最为宝贵的精神气象,诚因如此,他们的画作往往具有穿透生命的力度直抵人心。(作者:孙亚军,青年学者、作家)编辑:亚洲华语文旅卫视 曹琳